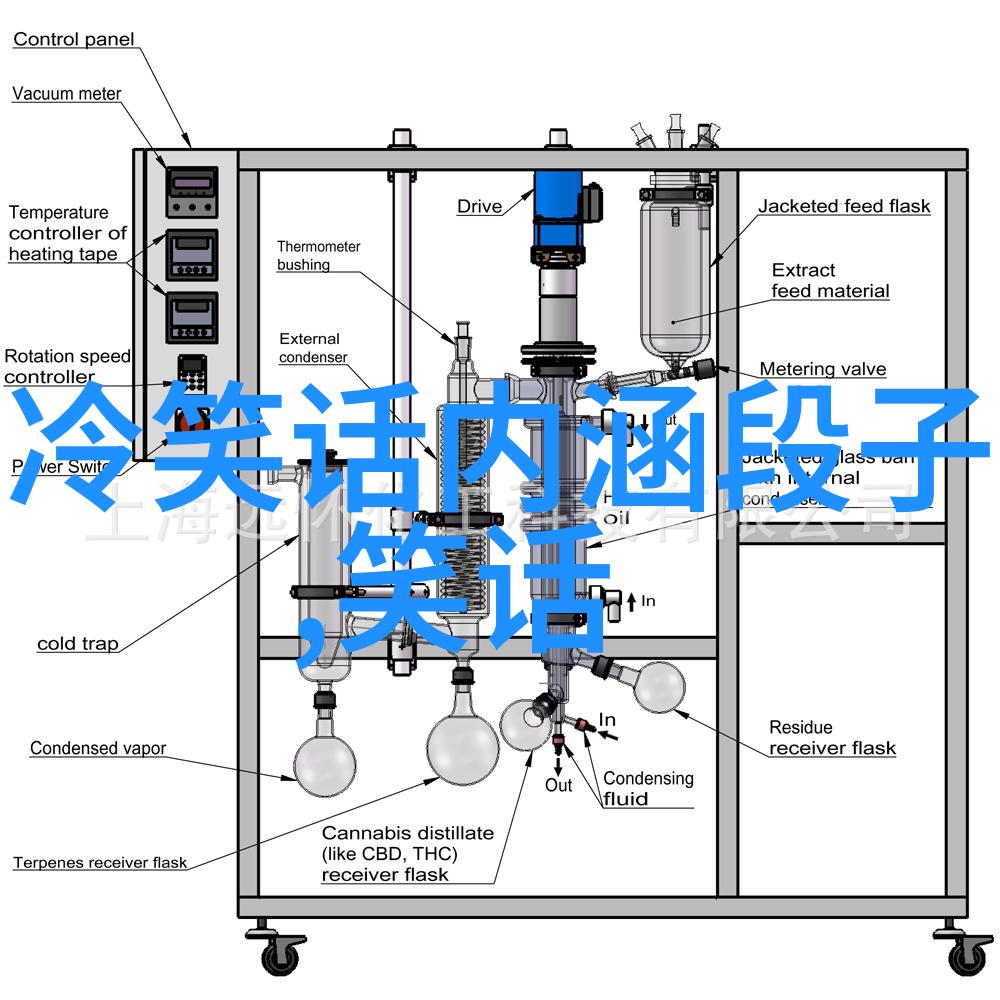1977年,高中毕业后,我下放到一个武岗大队插队落户,在大队林场当上了一名下乡知青。 说是林场,其实没有什么树木,只是一个荒土岗坡,茅草丛生,不长庄稼。把这里当成林场,主要是为了安排照顾我们十几个知青。大队里除了派来一个场长外,还配备了专门的炊事员,免得让我们这些从小跟在爸妈身边的人,连饭也吃不上。场长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复员军人,他看到荒土岗不长庄稼十分着急,就让我们十几个知青,每天挑着担子,到附近村里捡粪,用粪把荒岗死土盘“活”,然后种庄稼。 就这样,我们成了捡粪郎,每天挑着粪挑子,手拿着粪扒子,到附近村庄捡粪。捡粪不是那么容易的,因为那时化肥还不太普及,猪牛粪成了宝。平时,队里、家里的猪牛都圈在栏里养着,猪牛拉下的粪也就在栏里。所以,硬碰硬地去捡粪,一天根本捡不到多少。捡得少,自然工分也就挣得少。大家都是年轻人,好胜心强,谁也不愿捡得少。结果,为了多捡粪,我们就偷,趁村民不注意,到猪牛栏里偷。 这天上午,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挑着粪挑子,出去捡粪。这天的运气不好,快晌午了,我们还没有捡到多少粪。周围村民对我们有防备,只要看到我们进村,就有人跟在身后,根本不给我们进猪牛栏偷粪的机会。可是,我们也不死心,就这么空手而归,挣不到工分还没什么,关键是不能让别人笑话。 我俩挑着挑子,耐心地转悠着,等待时机。很快,我俩走进了一个小村庄,刚进村,就有个满头花白的村妇悄悄跟在身后,她拿一个木梳有一下无一下地梳着头,很悠闲的样子,显然这是专门来“盯梢”。不过,我俩还是暗自高兴,因为村妇年纪大,如果我们瞅准时机,乘其不备,钻进猪牛栏里,三下两下粪挑子就“捡”满了。 于是,我俩跟村妇玩起了“捉迷藏”,一会往东,一会往西。村妇也很有耐心,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,就是不给我们机会。 这时,我们看到前面有个大牛栏,里面牛哞哞叫个不停,老远就能闻到牛粪浓重的臊味,同伴向我使了眼色,我心领神会,准备来个“速战速决”,冲进去硬抢。可是,还没等我俩走进牛栏,那个村妇已看出我俩的企图,抢先一步,走进了牛栏,不住地往牛槽里添加草料。我俩懊恼不已,心里骂着村妇。这时,村妇忽然急急忙忙从牛栏里走了出来。趁此机会,我俩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,抡起粪扒子,把一摊摊牛粪扒进自己的粪挑子里。牛栏里粪真多,没有几下,我俩的粪挑子就装满了。 大功告成,我俩忙不迭地溜出牛栏,小跑着出 了村庄,准备回林场。可是,刚出村。我俩忽然发现刚才那个“盯梢”的村妇,又跟了上来,嘴里还不住地叫我们等等。偷粪这事能等吗,这虽算不上犯什么大错,但也不是光彩的事,她如果再把我们好容易“捡”来的粪收回去,岂不白忙活一场。 于是,我俩挑着粪挑子,大步走着。为了迷惑村妇,我们没有直接往林场走,兜着圈子在空旷四野里转悠。我俩年轻,脚腿麻利,跟那个老村妇兜一阵子后,她就会放弃的。那样,我们也就可以轻松地挑回那一挑子粪。 可是,那个村妇却穷追不舍,紧紧跟在我们身后。虽然追不上,却像影子似的总也甩不掉。我心里叫起苦来,偷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还是头回遇到这么难缠的人。眼看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,我们挑着粪挑子,已经转了半天,又累又饿,实在也是没有力气跟老村妇兜下去了。 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,对同伴说:“算了,我们回吧。” 同伴喘了口气。说:“可是,她要是跟着我们到场里怎么办?” 我想了一下,说:“随她,场里人人都偷粪,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了不起,让她把粪拿回去。” 这么一想,也就有些理直气壮了,我们挑着粪挑子回到林场。没想到,前脚到,村妇后脚就跟了来。得知这一幕,林场的知青,都跑出来看热闹,偷粪让别人追到林场,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。 我俩已经做好了跟村妇舌战一番的准备,无非是死不认账,胡搅蛮缠打横炮。等我俩把粪挑子放下,村妇三步并着两步快步走到我们跟前,什么话也不说,伸出双手在臭气熏天的牛粪里翻找起来。我愣怔住了,睁大眼睛,疑惑不解地看着村妇在脏兮兮的粪里翻来扒去。 村妇翻找完一个粪筐子,又到另外一个粪筐子里翻,连着翻找了三个粪筐,最后终于从一只粪筐子里扒出一个已经断了几根齿的木梳子。 村妇拿着找到的木梳子,红着脸说:“跟你们说实话,队里是让我跟踪你们,阻止你们偷粪,给我算一天的工钱。刚才我看到你们要硬进牛栏捡粪,就先进去装着给牛喂草。结果,一不小心把梳子掉在地上,正好一头牛拉屎,把梳子给盖上了。我出来准备找个东西,捞出木梳,没想到,你们手快,竟把那泡牛粪给扒走了。没别的,我追你们就是要找回我的梳子。” 有个知青听后,哈哈大笑,说:“不就是一把破木梳吗,值得你费那么大劲?” 村妇说:“你不知道,我一天工分才五分钱,而这把梳子要五角钱,今天我就是没工分,也不能丢了梳子啊。” 说完,村妇面带喜色地离开了林场。 看着村妇的背影,我们十几个知青都愣住了。从此以后,我们这些知青再也没有人去偷粪,宁可一天空手而归。

标签: 超短的冷笑话 、 一千个爆笑脑筋急转弯笑话 、 冷笑话段子爆笑简短 、 200个脑筋急转弯 、 幽默故事精选